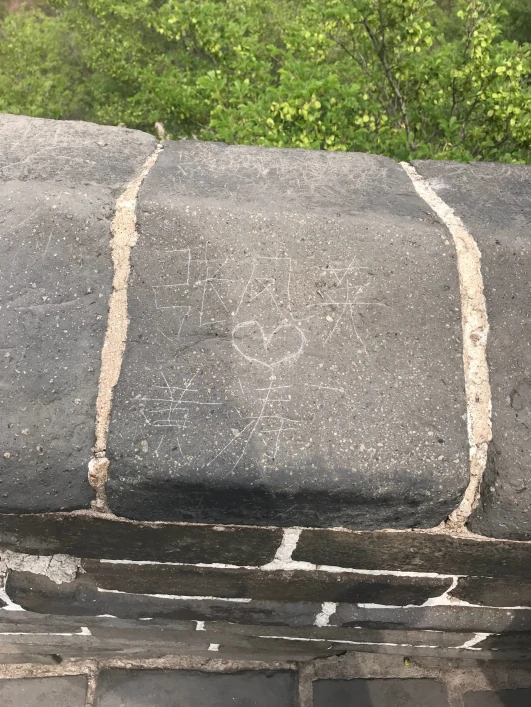1
标哥住在缅甸密支那市华侨新村,门前是早已更名的中山路,路对面有座华人的观音寺,发源于中国西藏的伊洛瓦底江从远处静静流过。
在标哥那所大院子里,泊着3辆军用道奇卡车,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驻印新军曾驾着它们冲过密支那的“十一条横街”防线,从日军手里夺下这座缅北重镇。
华侨新村是密支那战役最激烈的阵地,被两军炮火炸成了一片废墟。战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感念华侨的支援,安排部队的工程兵帮助他们重建了新村和华人学校。
如果是去密支那市,人们大多会找标哥帮忙;一听说是为着远征军的事,他比来访者还积极,撂下生意就当起免费的联络员和专职司机。2014年,他和云南同乡会的同仁冲破阻碍,在华人公墓为阵亡缅甸的中美英盟军和中国远征军立了忠魂碑。
标哥看上去像一个地道的缅甸人,上身着一件蓝格子衬衫,下身裹着像筒裙样的笼基,赤脚穿一双人字形拖鞋。
领队大鸟给大家介绍标哥,说他是中国远征军的后裔,在密支那的华人圈子里很有号召力,为了远征军遗骸归国的事情出了很多力。
标哥听了一个劲地摆手,“哪里,哪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黝黑的脸上肌肉有点僵硬,没有笑意,也并不冷淡,似乎天生做不出太多表情。
标哥祖籍河南洛阳孟津县,开口说话却是云南口音。后来知道聚集在华侨新村的华人多来自中国南方,有广东的、福建的、云南的――很多云南人从祖辈就来到缅甸做马帮、讨生活,只有零星的几家河南人、山东人,标哥只得并入了云南同乡会。
标哥的邻居还有尼泊尔人、印度人,近些年有的缅甸人也住进来,华侨新村俨然成了一个地球村。
2
第二天我联系标哥,打算去他家里拜访,可是没打通电话。我入住的酒店距离华侨新村不太远,又恃着前日刚刚去过那里,就决心自己摸路去找他。
密支那的街市如流经她的那条伊洛瓦底江般舒缓安静。街边英国殖民时期种下的金合欢树冠盖如云、古意苍苍,树干要两三个人才能合围。两旁边的竹木楼低伏于大树前,隐在繁茂的阴凉里。也有用砖石建造的四、五层高的新楼,很是显赫气派,仿着木楼修了坡顶,却仍显得粗糙笨重,缺了些灵气。
不管如何,每家的住宅都连带着一个宽敞的庭院,院中栽种了细高的椰子树,阔叶的香蕉树,屋后还有巨伞样的大榕树,一派蓊郁苍翠。
路上看不到公交车或出租车,路边停放着三三两两的大三轮车,车斗被棚起来,这是密支那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走了一路,也不见一个交通警察,但各样轿车、摩托车、自行车在路上同行并,看着杂乱,却也通行流畅,并不拥堵。
经过一个路口时,我看见那儿有个木支架,上面放着两个陶罐,里面盛满了清水,不知是什么用途。后来问了标哥才知道,那是僧人或店家置在那里供人解渴的。
行人都穿着标哥那样的人字形拖鞋,不紧不慢地走,迎面过来的一位男孩眼睛安闲平和,友好地对我点头微笑。
这里的人们大多信奉佛教,男孩必须送到寺庙做上一个时期的僧人,长大后才能获得尊重,才被充许从事体面的工作。
前一晚,我们在观音寺吃的斋饭,饭后一位10来岁的小僧人来收拾碗筷,我和他答话:“你会在寺里做多久僧人啊?”他很开心地回答说:“做一辈子的。”
女孩都扮了脸妆,用的却不是脂粉,而是香楝木做得香料,在脸蛋儿左右各涂成淡黄色的圆,既能防晒又能驱走蚊虫。一位安静美丽的女孩守在货摊后,摊子上却摆着一个恐怖的猴子头,她的货品还有装在玻璃瓶子里的老虎油,熊掌……各种稀奇古怪的野物。
3
因为走上了岔路,最后还是靠标哥接到了我,才到了他家。
标哥家的庭院本来也很宽敞,但院中盖了好几所房子,又停了三辆卡车,就显得局促。他开的那辆道奇,淡绿色的车身已经斑驳发黄,但骨架依然硬朗犀利。
我笑说:“您把这几辆车运到国内,卖给收藏家,说不准能卖个大价钱。”
他又摆手说:“喔,喔――这破东西,发动机早就换成日本的了。你看那后面的车箱,我改装成了翻斗,卸砂石方便。”
这车已经陪了标哥多半辈子,小时候他坐在父亲身边的副驾驶座上,15岁以后,开始独自驾车做运输生意。就像这车一样,标哥虽身材不高,身上却透出一股刚劲凛冽的气势,他的腮骨突出,棱角很分明,短髭浓密,再加上黝黑的肤色,整张脸便如金属塑造而成。
 伊洛瓦底江滩
伊洛瓦底江滩
标哥的父亲邓铸九是中国远征军驻印新军汽车六团的兵,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他随军在印度蓝姆伽接受了整编训练。1943年10月,中美驻印新军由印度利多反攻缅北,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越过野人山,血战胡康河谷,击败日军的“山地战之王”第18师团,以惨重代价攻克于邦、孟拱、密支那、八莫,荡平缅北日军。
邓铸九在家乡河南已经娶妻生子,打完密支那,他思乡心切,再也不想打仗,就偷偷离开了部队,逃到伊洛瓦底江东岸,打算待风头过后再返回家乡。可等到日本投降,国内又爆发了内战,中缅边境的形势更加凶险。
眼见回国无门,邓铸九只好作长久打算,把自己名子中的“铸”字拆分开,改名为邓金寿,在密支那华侨新村安顿下来。
打完仗,美国一家公司向民间拍卖军用物资,标哥的父亲邓金寿买下一辆道奇卡车做起了运输生意,也载人也拉货。因为那时汽车非常稀少,生意虽算不上兴旺,但足够应付生计。
过了几年,邓金寿仍然看不到回国的希望,也就狠心断了念想,娶了一位缅甸的傣族女孩为妻,在密支那扎了根。
当年远征军的汽车兵都是部队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多相貌堂堂,又有一手技术,脱离军队也不愁生活,所以留在缅甸的汽车兵很容易讨到老婆。
标哥的母亲生了7个孩子,父亲按照孔子教导的“恭、宽、信、敏、惠”为5个男孩命名,老大邓恭标,就是标哥。
4
留在缅甸的远征军只是埋头讨生活,很少向后辈谈起那场惨烈的战争。标哥也只记得父亲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整日辛苦奔波,一天也不舍得耽搁,别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他也接。
有人去世,尸体要拉到墓地埋葬,华人大多都不愿意做这样的生意,认为不吉利,是件丢脸的事,父亲却从不拒绝。信佛的母亲说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要多做才好。
标哥儿时的印象中,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就听到院子里马达轰鸣,车灯照亮了窗子,是父亲出门上路了。父亲一出去就是一大天,要晚上9点多钟以后才回来。
母亲在院子里种满了荔枝树,夏日他和兄弟们在树林里穿梭嬉闹、爬上爬下;到了采摘的时候,他帮母亲把那一串串玛瑙样的荔枝剪下来,拿到街边去卖。
有时候,母亲会带他去寺里烧香拜佛,为父亲祈平安,为孩子们祈福。后来标哥也信奉了佛祖,加入了密支那华人佛教会;屋子里的墙壁上就挂着教会公举他为常务委员的繁体字证状。
身在异域的人,要抱团才过得下去。密支那的华人除了同乡会、佛教会,还有青帮、红帮,是清朝时入缅的,起初也做些打打杀杀的事情,现在大多都有正经职业做、正经生意。标哥年轻时也焚香拜帖加入了青帮。
即便是这样,那时的华人也受欺负,他们被限制在伊洛瓦底江以西,过江要办通行证,为此标哥很少去江东的外婆家。“那时候老缅骂我们‘中国虫’‘臭中国人’……现在不同了,中国在缅甸有几百亿的投资,山上、江边的好多玉矿、金矿都是中国人在采……见到中国人要叫一声‘老板’‘大哥’……说起中国大陆,都觉得是天上一样。喔喔,不得了的。”
我笑着插一句:“并不是人人都在天上。”
5
到了读书的年纪,标哥进入了华侨新村的育成学校。这所华人学校里的教师有不少是孙立人当年留下的部队里有文化的将官,课程以教授国文为主,也有缅文、英文,当时国文教科书多是由台湾提供。学校里上课下课要敲钟,那口钟是二战时的炮弹壳做成的。
1962年3月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第二年,政府颁布企业国有化法令,将银行、工厂、商店全部收归国有,标哥就读的育成中学也被“国有化”,他喜欢的国文课被取消了。
 标哥与远征军后裔们
标哥与远征军后裔们
标哥在密支那的街头见到过周恩来总理,他来参加克钦族人的节日,被一群人簇拥着笑得很开心。
此时,标哥的一位邻居王连长――反攻缅甸时在驻印新军担任连长――正蹲在密支那的一所监牢中。王连长是亲台湾的“白派”,缅甸政府怕他在周访问期间闹乱子,事前就把他关进了牢里。台湾那方面有重要人物来访时,也会有亲大陆的“红派”被关押一阵子。
标哥的父亲很低调,只一心出力做活、挣钱养家,从不在外面乱说话,在这样的外事活动中总能平安无事。
1967年毛泽东像章传到了缅甸,标哥的很多同学都把它戴在胸前,很威风、很自豪的样子。标哥觉得好看,也搞来一枚挂在胸前,雄纠纠地回了家。没想到父亲看到他的像章立刻阴了脸,喊他拿了下来。
中国给反政府的缅共军队提供武装,建立了缅甸东北区,后来还有很多云南知青跨过边境“支援世界革命”,与缅共并肩作战。中缅政府积怨既深,缅人又受到那红像章的刺激,就把怨恨发泄到了华人身上。
暴徒们闯入华人的商店和住宅,财物被抢走,人被打死丢在街头,学生也不放过。“皮肤白一点的人都给拉出来杀掉(缅人皮肤黝黑),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那时的候华人好惨……”标哥不停地摇头。
6
我和标哥在客厅聊,从穿堂门里走进来一个人,是标哥家的老五,他的弟弟,邓惠标。
我想和他也聊聊,邓惠标一边偷眼看着标哥,一边拖把椅子坐下来。虽然他坐得很远,我还是闻到他身上有浓烈的酒味。
“我1987年去读台湾辅仁大学……我记得学校的地址――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510号。”邓惠标喃喃说道。
这个在自己家里都怯生生的人,读过台湾最顶尖的大学,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郝慰民是同系校友。
那时他已经在缅甸大学读了三年书,还差一年毕业,台湾辅仁大学来缅招生,他递了申请,被录取到化学系。标哥劝他拿到缅甸大学的毕业证再走,可他心气高,一心只想着去台湾,“我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在辅仁大学的一次聚会上,邓惠标操着吉它唱了首傣族民歌。一名来自台北的女孩被歌声吸引,成为他的恋人。
“她是大都市的女孩,家在台北市中正路……”虽然已经隔了20年,邓惠标还是说出了那女孩的精确地址,“有三层是她家的。”
他们相爱三年,可女孩的家人始终看不上他。
假期里,他追随女友来到台北,在全球最大的专业集成电路制造企业TSMC公司找了份工作,月薪有2万台币。
女孩的家人却为了摆脱他,举家移民到加拿大。他仍然不肯放弃,又飘洋过海追到加拿大温哥华,最终在那里接受了分手的结局。
失去女友后,他没有回到学校,也再无心工作,背着那把吉他黯然回到了密支那。
“读了两个大学,一个毕业证都没拿到。”标哥说。
回到密支那的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成家,和哥哥们一起住着。
“她曾经写信来,说找了个加拿大人做先生,生了孩子。现在,他们的孩子也该长大了。”
“你自己的婚事总不能一直耽搁着,也得娶个女人呐。”
“我现在这个样子,到哪里去娶?有女人肯要我,我宁愿‘嫁’过去。”
邓惠标蜷缩在椅子里,很困倦的样子。标哥赶他回屋睡觉。
等他走出去,标哥说:“跑了一大圈,落得这个样子。这是有客人在,我给他个面子,平时在我面前他坐都不敢坐。”
“他吃药膏,你看他那副牙,全是假牙,还不到50岁,牙都掉光了。”
“药膏,鸦片膏?”
标哥点点头。
 伊洛瓦底江的落日
伊洛瓦底江的落日
尾声
父亲邓金寿在心里一直没有放下留在中国的妻儿。有时标哥和兄弟们把他惹火了,他大骂道:“我一脚把你踢到天边去,要不是因为你们老子早就回国了!”
八十年代末,华侨新村有家人的孩子去河南读书,父亲给国内的妻儿写了一封信,嘱托那个孩子带到他的家乡,帮他寻访家人。
不久后的一天,父亲收到回信,一个人拿了信走出屋子,到屋后头去看。标哥偷偷跟过去,见父亲正握着那几页信纸掉眼泪。
“后来我一看信的落款是邓标――邓标是谁,哪儿来个邓标?”
邓标就是父亲离别了50年的长子。
此后,两边有了书信往来,但直到父亲去世,这对父子也没有见面。
几年前,已经70多岁的邓标来到密支那,标哥陪他去华人公墓祭拜父亲,一起在坟前磕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