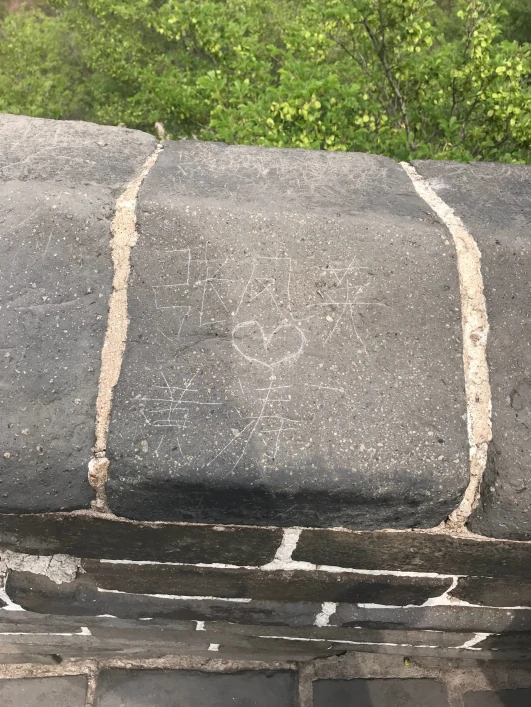1
心理问题是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的,就像感冒、腹泻一样平常,但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羞于启齿,拖延治疗,大大降低了生活质量,还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叫张颖,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有十年了。2019年春,我回到了老家浙江宁波,办起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
大陈是我在工作室接待的第一位咨询者,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位。那天,他穿一身得体的格子西装,略有些犹豫的样子,搓着双手走了进来。
大陈进来后有些不知所措,还没坐下,就嗫嚅着说:“市医精神卫生科的刘医师诊断我是焦虑症,让我来找你。”虽然有刘医师的大力推荐,但他还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来找我。
我引领他路过躺椅,坐到一张靠背椅上。我们成九十度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他靠在椅背上,两手相互揉搓着,不知从哪儿开始说起。我等着,希望由他选择话题。
从外表来看,他长相挺阳刚,标准的国字脸、高鼻梁,只是浓眉下的那双眼睛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我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为缓解他紧张的情绪,我主动问:“能简单跟我说说你的症状吗?”
大陈明显更焦虑、紧张了。他回答得很快,手肘靠在桌子上,身子前倾。他说自己经常感到胸痛,已有20多年了,近年来越来越严重。
天一黑,他就觉得紧张,害怕出门。夜里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是断断续续,常做噩梦。这些年他看过不少医生,但都查不出毛病。
陈述这些过程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所受到的折磨和痛苦。我帮助过不少像他这样的病人,也很有信心能帮大陈渡过难关。
“你说胸痛有二十多年了。请你谈谈第一次发生胸痛的情况好吗?”我尝试着去找找根源问题所在。
他告诉我胸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在母亲过世的那个晚上。虽然刚到初秋,但是那天天黑得特别早,他走出单元门时,一阵冷风灌进了衣服。突然,他觉得胸口一阵绞痛,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从那天起,他就特别怕黑。起初以为或许是受凉了,或许是给母亲办后事太累了,但后来隔三岔五地就会胸痛。
“愿意和我谈谈,母亲去世时你的感受吗?”我问。
“很难过。但是大家心里都有准备的,因为母亲患肝癌五年了,已经到了晚期。”他说。
“在这期间有没有发生过特殊的事?”
“没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么看起来,母亲的亡故不是导致疾病的真正原因。那么导致疾病的那个事件又在哪儿呢?我只有把网撒得大一些了,试图引导他去谈谈过去的生活经历。
2
大陈,197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收入不高。
他一直是村里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不说,而且没花家里一分钱。学费、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做家教赚的。
他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一双运动鞋穿得开了口子也舍不得买新的,去校外修鞋铺补了补,一直穿到了大学毕业。如果到了期末,手头上还能有些剩余,也都交给了父亲。
1998年,陈母因为肝癌晚期去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五万块的债。
毕业后,他为了给家里还债,放弃了家乡舒适的工作,当了北漂。白天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晚上接一些画图纸的私活来做。每晚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早上八点又要赶到工地上班。
五年后,他当上了项目经理。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父亲在2004年遭遇了车祸,多处骨折,身边需要人照顾。
这时候,姐姐已在上海成家了,他只好回了老家。后来,大陈拉起了一支建筑队,赚了些钱,他给父亲买了大房子,请了保姆。
他略带讥笑地说:“邻居、亲戚们都说父亲有福气,生了我这个大孝子。唉!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啊。”
“你觉得生活很苦,是因为觉得为了父母,你必须得要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我用提问方法,引导他去寻找内心的感受。
他往椅子背上靠了靠,微微抬起头,目光似乎在半空中搜寻着能帮助他的力量。过了会儿,他说:“没办法呀!很多事是很无奈的。能看着家里的烂摊子不管吗?心里过不去,也怕被人指责呀!”
“能跟我谈谈你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吗?”
“和女朋友分手。在北京时,我谈了个当地的女朋友,说得上是情投意合。因为要回老家,我们分手了。”说到这儿,他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我还是观察到那儿升起的些许水雾。
“那天她哭得很伤心。她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回老家?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呢?比如多寄一些钱、给父亲请一个保姆、多回家看看或者请一段时间假。”他顿了一会,自问自答:“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不回家,良心会过不去。”
“良心过不去”这句话总感觉在给我什么信号,我提问、倾听,努力地收集信息,试图找到那个导致他疾病的相关事件。
答案会不会在他的童年?大成在会谈中好几次说道“没办法、无奈”这两个词。他无力去改变现状,无力去觉察内心的感受。这会不会和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
2019年5月8日,第二次会谈,我尽量不着痕迹地引导他谈童年的经历。由于大陈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的少,他记不得童年有什么大的心理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我建议用催眠来追踪。
我告诉他,催眠是帮助病人找到遗忘事件的绝佳办法。它并不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描绘的那样神秘,只是一种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但它能成功地让病人追溯到童年,回想起早已遗忘却对现在生活投下阴影的经历。
即使我大力推荐,大陈还是表现出了抗拒,觉得害怕,没有同意。
3
为找出心魔,我们深入地探讨了他的感情、思想和梦境。他告诉我,连续几天他总做同一个噩梦。
在梦中,浑身插着管子的父亲总是突然坐起来,指着他骂:“你以为舍得为我花钱是孝顺,其实是在花钱给我买罪受,你妈还在天堂等着我呢。”
“父亲不是住在大房子,有保姆全天伺候吗?”我问。
大陈告诉我,两年前,他父亲因肺部感染,再次住进了医院。入院第五天,父亲眼看着不行了,眼珠都往上翻了。
医生问他,要不要救?要救,就要进ICU了。这么大年纪进去了,也不一定能平安出来。像他父亲目前的情况,每天的治疗费用肯定要上万。
他想都不想,就说:“救,救,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救。”亲戚们又夸他是个大孝子。
但是当大陈去ICU看父亲时,他的心都碎了。他看见父亲的手脚被捆绑了起来,身上挂满了仪器和管子。因为插着呼吸机,父亲不会说话了。父亲微闭着眼睛,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
大陈喊了声“爸”。父亲微微睁开眼睛,眼泪就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姐姐看了也哭。她呜咽着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还不如让他爽爽气气地去了。”
大陈每次去看父亲,心都会揪起来痛。从那以后就开始噩梦不断!
每次从梦中醒来,大陈都觉得冰冰冷冷的,衣服都被汗浸湿了。他觉得四周的黑暗,就像一床浸湿的大毛毯压过来,让他透不过气来,很可怕。
他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神,言辞恳切地说:“为什么总做这样的梦呢?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呀!光父亲的医疗费,我就花了一百多万。至于他受的痛苦,我也无能为力呀,我让他活着了呀。”
因为这样的梦境,大陈的胸痛越来越厉害了,小姨迷信地认为是不是大陈天堂的母亲来找他了,甚至带他去母亲墓上烧了纸钱。可依然不奏效,甚至越来越邪门!
咨询做到这儿,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堵墙。对于导致他胸痛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头绪,总感觉它就在那了,但又够不着,翻不过去,不管怎么做,它仍然高得让我们爬不过去。不过随着挫折感来临,我更有一股不善罢甘休的决心。
我再一次劝说他接受我的催眠咨询。我告诉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可能因为心理的防御机制,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在我们的意识层面遗忘了。
但它还存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绪。
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一件创伤性事件被他遗忘了,而他的躯体和情绪还清楚地记得。
“如果你因为不了解催眠而感到害怕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下次咨询的时候先体验一下催眠,再考虑接受,还是拒绝。”我用真诚的目光看着他,期待着他的回答。最后,他答应考虑一下。
这个考虑的时间很长,大概一个月后,大陈才再次过来咨询。
2019年6月,大陈第三次来时,臂上带着黑纱。他告诉我,父亲已经走了,不用再受折磨了。他前一天刚去公证处,公证了自己的遗嘱。大概意思是:如果他病重到无法医治,一定不要过度医疗,让他平静且有尊严地走。
他释然地笑了笑说:“有了这个东西,既能让我活得安心,将来也不会为难儿子。”
通常病人能倾诉自己的不愉快,并能从更大更远的观点来洞悉这些事,总会进步很多,但大陈没有。
他告诉我,他仍然深受焦虑和痛苦的折磨,他还是怕黑,时常胸痛。因此,他答应尝试一下催眠治疗。
4
我用渐进式放松法,将他导入催眠状态,再用光照法深化催眠。他的全身在松弛安详的状态中慢慢放松了下来,随着我的口令,我能感觉到他已进入到适度的催眠状态。
我用催眠回溯技术,让他的思绪自由地漂浮。他反应胸口很痛,面部肌肉开始抽搐。我问:“你看见了什么?”
“我,我看见了姆妈。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我却没有救她……”说着,他大哭起来,越哭越凶,还用拳头拼命捶打躺椅。
我知道,我既要让病人充分宣泄情绪,又要把握好度。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心脏在急速地“怦怦”跳动。
我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我要保持冷静,维持一种空白的心理状态,让病人能自在地倾吐他的情绪、想法和态度,然后再仔细分析其中的曲折。他发泄了一阵后,慢慢平静了一些。
我用平静且温和的声音说:“能和我说说你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吗?”
他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
“如果你想倾诉,现在可以说出来,这里很安全。”我耐心地鼓励他。
他用虚弱的声音缓慢地说:“这天我坐公交车回家。刚下车就看见附近彩票销售点前,有几个人在高声谈论着什么。我鬼使神差就走了进去。销售员笑眯眯地问我,要不要买一组?”他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我问:“你买了吗?”
“买了。我用口袋里仅有的两个硬币,机选了一组。结果中了五千元。”他继续说,“我高兴极了。觉得老天爷在眷顾我,特意给我一笔意外之财,让我买手机。我到手机店,选好了一部黑色的摩托罗拉。”
“要付款时,我突然想起重病的姆妈和家里欠的债。我赶紧说:‘对……对不起……我有些急事。明天再来……’我飞快地跑了出去。天正下着大雨,我没有撑伞。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姆妈躺在医院里,我怎么可以拿这钱买手机?”
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似乎在做一个困难的决定。然后说:“最后我想,反正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毕业后,好好赚钱,帮家里还债。再说,五千块钱对姆妈的病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想着,第二天我去买回了手机。”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引导他进入下一个场景。
“我赶到医院,看见母亲双颊凹陷、脸色蜡黄,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和仪器。走廊上,父亲焦急地踱着步。没几天,姆妈就走了。是我害死了她……我不是人……”说着,他抽泣起来,或者说嘤嘤地小声哭了起来。
催眠状态下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我面前失态,展现着自己完全真实的、没有任何掩饰的一面,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等着他释放,然后再慢慢引导他走出睡眠状态。
醒来后的大陈,用手摸到眼角的泪水略有些尴尬,催眠后会谈,我尽量让他去回忆催眠时,他告诉过我的事。
为了让他彻底打开心结,我问:“假设你没买手机,钱交到了医院,你妈能用上吗?她的生命能延长几天吗?”
他愣了一会儿说:“用不上,记得当时出院的时候,预缴的费用还有余额。”回答完之后,他再次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魔所在。
5
最后一次治疗,我试图把他催眠到深睡眠状态,引导他和他母亲见面,试着做一次告别,试着引导他寻求母亲的原谅,也让他与自己和解。
我让他躺在躺椅上,头枕在小枕头上,眼睛微闭。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每次吐气都释放出一些长期积压着的焦虑,每次吸气又放松一些。
“我知道你的潜意识充满了智慧。它会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会看见一件神奇的事情将要发生。”我问,“你看见了什么?”
他说:“我看见了一条蛇,盘在我的胸口。”
“这时,你发现那条蛇,离开了你的身体,它会带着你开始你的旅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继续引导。
“它在我前面,很快地游走,像飞一样。我跟着它正穿过树林。”
我说:“等你停下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看到了什么?”
“我来到了一个隧道口。那条蛇不见了。哦!它变成了一列火车。”他说。
“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知道火车会带你去什么地方。”我轻声继续地引导。“我坐在火车里,列车穿过了黑暗的隧道。天越来越黑了,它跑得很快。”他形容着。
“它停下来时告诉我,你到了个怎样的地方。”我说。
“火车停下来了。那里有一座座墓碑。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公墓。对面走来了一个人,但是我看不清……”此时,我看见大陈呼吸有些急促,眼角流泪。
我问:“一个黑漆漆的晚上,在墓地里,会是谁呢?”
“一个骷髅,它向我走过来。”
“你是什么感觉?”
“我胸口很痛。我看清楚了,啊!她是我姆妈。姆妈……姆妈……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骂我,你打我吧!我胸痛了二十多年,是老天在惩罚我……一定是老天在惩罚我……”
他泣不成声,面部肌肉猛烈地抽搐着,嘴里喃喃地连续说着忏悔的话,眼泪成串的滑落下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过了一会儿,我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他吸了吸鼻子说:“姆妈原谅我了,她很高兴。咦!她不再是骷髅了,变得有血有肉了。”
“好,非常好!现在你拥抱一下姆妈,告诉她,你非常地爱她。在你的心里,永远有她的位置。”我引导他和母亲告别,“要跟姆妈告别了,听听姆妈还想跟你说些什么。”
“她希望我能很快康复,幸福地生活。”他说。
我看见他脸上的阴霾,在慢慢地消散。
我温和地告诉他,那些经历都过去了,都结束了。他现在安静地在休息。然后我把时间向后推,推到他现在的年龄,指引他苏醒。
最后,我教会了他自主放松的方法,给了他一些良性暗示。
6
经过这次催眠回溯对话,大陈宣泄、疏通了情绪,也重新理解、评判了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
大陈回忆说,他母亲很能干也很强势,经常抱怨父亲不求上进,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和姐姐身上,尤其对他特别严格,经常告诫他不能像父亲那样没用,男子汉要撑起一个家。
五岁时,大陈和邻居家孩子抢糖吃,母亲看见后骂他没出息,拉回来就罚跪。跪了老半天才允许起来,起来时两条腿直发抖,站都站不住。
读书了,每次考试成绩,他必须在全班前三名。三年级的期末,他数学考了八十八分,母亲拿起竹丝就抽,抽起来的红印子好几天才退。后来他成了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考进了重点中学,又考进了重点大学。
母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他对母亲谈不上特别有感情,也从没意识到,自己20年的胸痛症结点是在母亲病逝前,自己意外获得5000元偷偷买了手机而没有将这笔钱用来挽救母亲。
大陈将母亲的病逝在潜意识里面归结于自己最后没有出手相救,即使他知道那5000块钱于事无补,但总是在心里过不去,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了带给他胸痛20年的症结点。
这些年,他把对母亲愧疚的爱,加倍地用在了父亲身上,父亲生病需要他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放弃了北京的生活和女友,独自回到了浙江。
事业有成后,首先给父亲买了大房子、请了保姆全天伺候。
父亲两年前重度感染肺炎之后,他二话不说就要求抢救,即使过度医疗的父亲受尽折磨,他也希望继续用钱来挽救父亲。
在潜意识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把对母亲缺失的那部分爱,在父亲身上努力进行补救。
催眠后的会谈,大陈似乎轻松了很多,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张医师。我的胸痛明显减弱了,以后再也不用来你这儿了。”
我们又一次握了握手,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的坚定和力量。阳光正好,我目送着他的背影走出胡同,汇入了喧闹的人流。
后来,大陈告诉我,他助学了两个广西的贫困大学生,周末会去社会福利院做义工,忙碌起来的公益事业让他倍感安心,也没有再犯过胸痛的老毛病了。
【本文来自知音旗下公众号:知音真实故事 ID:zsgszx118,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