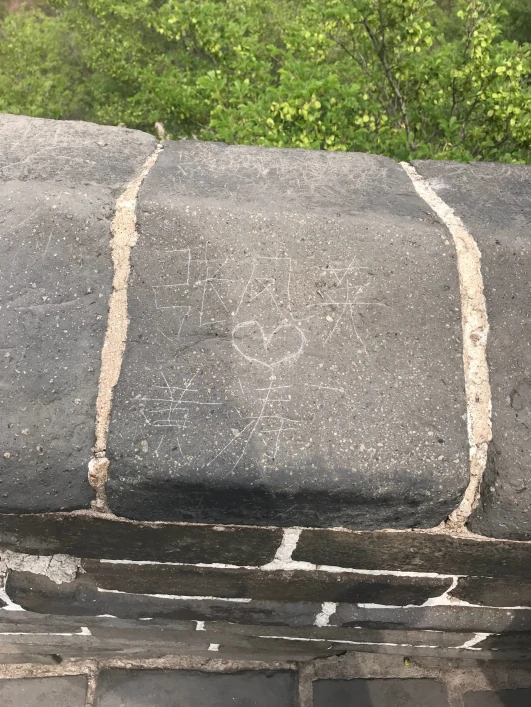1
2013年12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厨房做饭,儿子飞飞和几个小伙伴,在楼下的空地上玩耍。我家住在三楼,厨房窗口恰好对着这片空地。偶尔,我会探身看看儿子。
忽然,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惨叫,好像是儿子发出的,紧接着是其他孩子此起彼伏的尖叫。我朝下一看,只见飞飞侧身躺在地上,其他人正从小区的不同方向朝他跑去。我头皮一阵发麻,赶紧冲下楼。
我冲下楼时,儿子已经被大人和孩子们围了好几层,有人在打急救电话,还听见有孩子大喊:“是他,是大虎砸的石头!”
我嚎啕大哭,握紧儿子的手,趴在地上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他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回应。鲜血从他的发间冒出来,流到脸上、地上,我脱下外衣试图捂住止血,可根本无济于事……
我叫罗丽娟,今年40岁,出生在山西阳泉市周边的农村。初中毕业后,我在附近镇里的制衣厂当针车工。2000年,通过媒人介绍,我和同乡陈建结婚,他比我大3岁,在镇上做装修工作。
和我家一样,他的父母也是农民。婚后,我俩在镇上租了一间50平米的小屋子。两年后,我们有了儿子飞飞,我辞掉了制衣厂的工作,留在家里专心照顾他。
因为生活开销变大,陈建想着找个更赚钱的工作,便去给一个煤老板当司机,家里慢慢有了点存款。
儿子刚上小学时,我动过重新工作的念头,和几个姐妹跑去北京学习做家政服务,考取了育婴师资格证,每个月能挣三千来块钱。
然而闯荡的心,最终敌不过对父子俩的牵挂,不到一年,我就回了老家。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拿出全部积蓄,在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砸伤我儿子的大虎是对门邻居的孩子,他的爸爸姓张,在镇上有自己的公司。大虎妈妈能说会道,跟谁都是自来熟。她家里的装修和摆设很有排场,形形色色的朋友常去他家打牌到深夜。
大虎和飞飞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两人经常一起玩,我们大人自然也熟络起来。有时,邻居回家晚了,我就让大虎来我家吃饭。
大虎贪玩,学习一直吊儿郎当的,是学校里有名的小霸王。他父母很少管他,有时我想劝他们多留点时间给大虎,可每次见到他们趾高气昂的样子,到嘴的话就都憋回去了。
没想到,今天大虎又玩起了恶作剧,从他家向下扔石头!据现场的小朋友说,儿子当时正在和其他孩子说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飞来的横祸。
情急之中,我顾不上报警,也没有想着拍照取证,只打了120。
镇上的医院离我家很近,没几分钟,急救车就来了。随行医生检查了儿子的状况,当即决定送他到县中心医院。
大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站在外圈不敢靠近。有邻居给他爸爸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回来。
2
路上,我打电话让老公尽快去县医院。当时他正开车送老板去饭店应酬,因为担心他行车安全,我没敢说出儿子的具体情况。
到了急诊部,头部CT检查显示,儿子的伤情为开放性颅脑损伤,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直接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说,必须立刻进行开颅手术!
我被吓得手足无措,手术知情书签字时,手抖得根本不听使唤。
陈建和大虎爸爸陆续赶来。大虎爸爸说:“对不起啊,大虎肯定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这次手术费都算我们的,我有亲戚在这家医院,关键时肯定能帮上忙。”
我老公向来脾气好,没见他大嗓门冲人发过火。果不其然,此刻他依旧忍着怒火,涨红着脸,一字一顿地说:“老张,大虎顽皮,这你们是知道的!事到如今,只要孩子没事,我们先听医生的安排吧!”
手术过程很顺利,我和老公不停地对医生道谢。
三天后,飞飞苏醒过来。当看到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孩子,现在脑袋裹满绷带,看不见眼睛,全身上下插着好多条管子,家人们都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大虎爸妈也在。主治医生把我们叫到一旁说,开颅手术是非常大的手术,孩子要在医院住满三周,随时观察生命体征,还有给予脱水、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预防并发症。
“三周?要住这么久!”跟出来的大虎妈妈一下子跳出来。他老公瞪了她一眼,冲她一个劲儿地递眼色,她才把下面的话憋回去。
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医院。
第十天,孩子拆完线,医院通知我们:这几天要安排出院。我吃了一惊,孩子现在还很虚弱,说不清话,无法正常进食,每天都在输液,怎么这就能出院了?
儿子会不会有后遗症?他以后的学业、工作、甚至婚姻,究竟会不会受到影响?我忧虑不已。医生安慰我们说,回家慢慢养也可以的。我和老公性子软,也不希望为了多一个星期,而让张家指责我们多花钱,便同意提前出院了。
出院当天,大虎爸爸一改曾经亲热的语气,板着脸对我们说:“咱们就算结清了,以后孩子有什么事,都不要再找我们了!”
我拽拽老公的衣服,想让他说点什么,可他不吱声。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话:“老张,你看孩子受了这么大罪,也这么快就出了院,你们能不能再多给一点营养费,这之后的花费,还非常多……”
没等我说完,他立刻打断我:“这不可能,你们不要没完没了!”转身便扬长而去。
3
儿子仿佛又回到了小婴儿时期,我要用长把勺把食物一口口喂到他嘴里,再轻轻地擦去顺着嘴角流出来的汤汁。除了补充营养,还要定期带他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因为晚上也需要照顾,我们夫妻两班倒,有些吃不消。很快,为了儿子,陈建辞职了。
在我们无微不至地照料下,飞飞说话日渐清晰,走路也平稳了。可他每天仍是头痛欲裂,且拒绝吃止痛药,说怕影响大脑恢复。多少次,他疼到把头往墙上撞,我紧紧地按住他的身体,任凭他把我的胳膊掐得紫红。
有亲戚说,要找大虎爸妈要补偿,可我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飞飞慢慢好起来,也不想跟邻居撕破脸。哪知三周后的一个早晨,大虎爸妈重重地敲我家门。这是我们回来后,他们第一次上门。
“学校给娃们上过保险,你知道吗?保险金应该给我们,是我们掏了手术费!”大虎爸爸沉着脸冷冷地说。
我被问懵了。我隐约记得,学校给孩子买过保险。可到现在,从没有老师来提过赔偿金的事。
他见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更是抬高了嗓门说:“你们赶快去打听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们!”
大虎爸爸一走,我便询问保险公司。对方听了我的叙述后,说这是一场涉及第三方的意外事故,并不在理赔范围内。
大虎爸爸再来时,听到这个结果,竟说我是在敷衍他。他说,能不能理赔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我们必须先把钱还给他们。
我据理力争:“是你家大虎把我们儿子砸伤的!”话音未落,他便大声指着陈建的脑门说:“不给钱,我们就没完没了,一直闹到你们给了为止!”
那之后,他们时不时地来我家催款。
持续的骚扰,让儿子无法安心休养,我们只好把他送到村里的公婆家,再由我和陈建轮流过去照顾。我想,毕竟那些人还不敢直接到老人家里胡闹。
万万没想到,大虎爸妈竟找了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来我家做工作:“为了这一万五的保险金,你们别给老家人找麻烦,赶快把钱给老张,把事情了了!”
我满腔怒火,把水杯重重地摔到桌上,却无言以对!我和陈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一度怀疑,难道真是我们的错?可明明是他家大虎砸伤了我们的儿子啊!我们决定咨询律师。
我们找到曾帮陈建老板打过官司的刘律师。刘律师安慰我们说不要慌张。首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是合理合法的。退一步讲,就算可以理赔,受益人也是我们,否则,岂不是等于花钱让别人打自家孩子?
他还鼓励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孩子,起诉张家赔偿我们所有的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等。
刘律师给我们计算了代理费、诉讼费等各种费用,我和陈建一听,面面相觑,犯难了。
这几个月,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买房时又用掉了所有存款,现在生活捉襟见肘,甚至向亲友借钱以维持正常开销。哪里有钱请律师呢?
于是,我心一横,硬着头皮跟老公说:“我自己上!”
2014年4月,在刘律师的好心指点下,我们磕磕绊绊地捋顺了上诉状的内容,正式向法院递交了材料,法院很快立案。四天后,张家人签收了应诉材料。
一场苦战就要开始了。我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尽快打工挣钱,但我心里放不下儿子。
刚刚重返校园的飞飞,偶尔还会头痛,为了遮蔽疤痕,他整天带着帽子。得知我又要去北京赚钱,他懂事地说:“妈,你放心,我和爸能照顾好家。班上的几个好同学,都要帮我赶功课呢。”
于是,五一期间,我去了北京的一家家政公司。陈建留在老家,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官司。
4
很快,一个叫小洁的年轻妈妈面试了我。经理告诉我,这个客户的要求很多,很多育儿嫂都不愿意去她家做。
我说:“只要能赚钱为儿子治病、打官司,要求再多,我也能做好!”
或许是随了眼缘,小洁雇佣了我。
小洁是全职妈妈,怀了二宝后,经常生病,情绪很差,有时十几天都不下楼。她的抑郁,我看在眼里,也愁在心里。每逢天气好,我就主动拉着她一起出去。为了逗她开心,我还专门找些有趣的新闻,讲给她听。
她的大宝豆豆,性格活泼,每天登高爬低的,一刻不闲。我原本就喜欢运动,带着豆豆得心应手,豆豆很快就喜欢上我,这让小洁长舒了一口气。
很快,我就融入了这个小家的生活。小洁有什么烦心事也愿意和我聊了,大多都是家庭成员间的小矛盾。我开导她,只要豆豆健康,别的事情都不要紧。
然而,我从没有和她讲过我家的事。每个月收到工资后,我就立刻转给陈建。
另一边,陈建像保镖一样,每天接送儿子,从爷爷家到学校,寸步不离,以提防大虎和他的几个小跟班,给儿子使坏。
在学校,他们没少找茬。有人会趁着课间,猛然把飞飞的帽子拽下来,踢得老远,有人会偷偷地把儿子的课本撕掉几页。儿子心知肚明,并没有多理会他们。
陈建多次找到老师反映情况。然而,每次那些臭小子不过是接受一番口头教育,没过几天,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有一天深夜,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了我。原来,张家雇了两个人高马大、露着花臂的“社会人”,在半夜一点,敲开了我家的门,进去就是一通乱砸,临走前,还气势汹汹地抓起陈建的衣领,要求我们必须撤诉。
听着电话那头陈建发抖的声音,想着家中的一片狼藉,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气得血管一跳一跳的,对陈建说:“不怕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还能让恶人作了我们的主吗?”
之后几周,他们多次在深夜来我家狂敲门,陈建为了不影响别人,还是开了门。他们除了能在所剩无几的家具上狠踹几脚外,也只有无功而返。
张家一边对付我们,一边暗自把更多的石头“横”在了官司前面。在取证阶段,陈建恳求邻居们能够证明当天的经过,指证是大虎砸了飞飞。
哪知他们要么一口回绝,要么用各种原因推脱,说无法做证。就连那天脱口而出“是大虎”的孩子,也被父母送到亲戚家住了。
连续遭遇碰壁,让老公沮丧不已。从邻居们为难的眼神中,他猜到,肯定有人抢在他之前找过他们。
听到这些,我气得火冒三丈,在电话里指责陈建怎么没有早做准备。
他顿时发了飙:“我不懂,那你呢?你又管什么事了!”我们第一次因为官司的事争吵起来。
我更是生自己的气,连真话都没法替儿子讨回来!我顾不得自己的那点胆怯之心,立刻给刘律师打了电话。
一听是我,刘律师叹了口气说,陈建刚刚与他通了电话。他说:“你们夫妻两人必须镇定下来,研究清楚诉讼流程。在举证期满前,要抓紧去申请法庭取证!”
我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立案时,法院给我们的资料里明确列出过这一步,而我一头雾水,根本没有多读那些资料。
紧赶慢赶,陈建总算在规定时间内,把申请法庭取证的材料递上去。最后,通过法院办事人员在小区里实地核查,我们总算得到了宝贵的证词。
我忐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
那之后,工作之余,我开始通过网络、看书,搜集法律知识,我还专门用一个记事本写下诉讼流程和重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厚着脸皮向刘律师讨教,生怕再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耽误了大事。
到后来,刘律师都开玩笑,说我可以参加司法考试了。
5
那些日子,还发生一件让我啼笑皆非的事。
老家亲戚告诉我,张家人在小区里散播流言,抹黑我的人品,说我在孩子出事之后,还往外地跑,肯定有问题。
我做人一向清白,结婚这么多年,我原以为这种事根本无需我多做解释。我一笑了之,而陈建也只字未提。
十一长假,我回到家。仅仅半年,我家变得破烂不堪,脏兮兮的地面上有碎玻璃渣子,满桌堆着文件纸张,厨房的油渍也蒙上了一层黑泥。看起来,陈建很久都没在家做过饭了。
趁着儿子不在,我一边打扫房间,一边和他谈起官司,最后,说到了关于我的流言。
正当我不屑于继续这个话题时,猛然间,陈建再也克制不住情绪,顺手抄起身边的椅子,暴风骤雨地砸向了家里的一切。
伴随着我的惊叫声,他怒吼着质问我:“你说!那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你的钱是哪里来的……你立刻回家!不能再出去了!”
我跑进儿子房间,放声痛哭起来。我自责没有能力保护好儿子,被肇事者步步紧逼;更伤心的是,在我筋疲力尽时,连老公也怀疑起我。
飞飞回来时,我和陈建已无语多时了。
我一把抱住儿子,他闭着嘴不出声,可眼泪哗哗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是不是想妈妈了?”我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陈建一直垂着头,在角落里坐着。这时,他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们母子,全家人失声痛哭起来。我们都明白,十几年的夫妻,怎么可能不了解对方的为人!
他的这一次爆发,砸醒了我们。
我们意识到,为了打赢官司,我们不能总被动地让人拖着走,要直面所有的困难,积极地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陈建愧疚地恳求我原谅他。第二天上午,他破天荒地跑到镇上的图书馆,开始学习,查阅法律类的图书,希望能够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有所帮助。
我回到北京,除了关心儿子,也不再忽视老公,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能够时常感受到我的牵挂。
2014年秋,终于要开庭了,我不得不向小洁告假。
我给小洁讲述了实情。她惊讶地看着我,因为她从未察觉到我有什么心事。
“罗姐,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应当早点告诉我,我还能帮到你!”小洁多给了我三天带薪假。她让我遇到麻烦时,一定给她打电话。这让我倍感温暖。
再一次回到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成了一个更好的妈妈,但一步步走来,让我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坚定。
6
开庭前,我整夜未眠,在心里不停地背诵发言稿——我要亲自上阵为儿子辩护!
第二天,我和陈建一同坐在原告席。邻居夫妻坐在对面,脸色铁青,狠狠地瞪着我们。旁听席上,我们双方爸妈正襟危坐,他们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在今天这片肃静中,他们比我更紧张,像是一场面对青天白日的宣誓。
轮到我发言了,我用力捏紧衣角,怕对方感觉到我全身的颤抖。
当我提到孩子头上那道十五公分长的疤痕时,不由得泣不成声。好多计划说的话,忽然都缠成一团乱麻。
辩论阶段,对方律师说着大段的专业术语,我完全怔住了。脑子绕不过弯来,只有直截了当地问他:“律师同志,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么多道理,我就想知道,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打伤人,你会不会补偿别人?”
律师停顿了两秒,不由得晃动了一下身体。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又继续他的发言。他那一瞬间的迟疑,竟让我有了一点点的胜利感。
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第一次庭审后,又有了第二次庭审,第三次,第四次……我一次比一次放松。我知道,这场官司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证人、伤残证明、票据明细这些证据在说话!
2014年12月,正像全家人坚信的那样——事实大于天。法庭判决对方赔偿我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和精神补偿费等,共计十二万元。
判决书拿到了,我却说不上开心,因为我紧绷的弦并没有放松。我猜测,张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三周后,他们提出要重新商议,只能赔偿五万。我老公坚决不同意:“这是法院判的!凭什么能改?”
我们甚至做好准备,如果由于对方拒付而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就算我们收不到一分赔偿金,他们也必将受到其他的惩罚。
当时,我早已返回北京。小洁生了二宝,家里的事情更多了,每个人都很疲惫,谁也没多提官司的事。
直到三个多月过去了,赔偿的事始终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法庭的工作人员叫陈建过去谈话。说张家难缠,如果现在拒绝了这五万,强制执行阶段可能会更麻烦。
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忍不住和小洁商量起来。她听了义愤填膺,主动提出要联系她在当地的朋友,看能不能帮忙。我连忙道谢,回绝了她,我不希望我的家事,再牵扯到更多的人。
那段日子,我时常翻看手机里与儿子的对话。飞飞期末考试进入年级前十;那些坏小子得知我们打赢了官司,又看到飞飞的状态越来越好,就都消停了;飞飞日渐浓密的头发已经遮住了疤痕……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不愿再这样对峙下去了。2015年深秋,我们接受了那五万元,并用这笔钱,偿还了所有欠款。
之后,我向小洁辞职,我要回到儿子身边去!小洁说:“大姐,之前我抑郁了,其实是你的行为一直在鼓励我,走了出来!作为妈妈,我支持你!”
持续两年的噩梦结束了,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吃上了团圆饭。
2016年初,陈建找了一份开工程车的新工作。我则去阳泉市的职业培训机构,考取了母婴护理证和月嫂证,在市里做了月嫂。每个月下户后,能回镇上陪家人几天。
在镇上人看来,家政就是简单伺候人,没什么技术性。但是,正是当年我的法律记事本让我明白,“专业”两字的重要性。
2018年,因为小镇旧房拆迁,我们在阳泉市郊分得一个新房,离市中心很近。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在市里开了家政公司,吸引更多的好阿姨加入这个行业。
虽然在创业初期,遇到不少障碍,但对于经历过生死之痛的人而言,拥有工作之苦真是一种幸福。
今年9月,儿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他笑着对我说:“幸好当初我不小心听到医生说,总吃止痛药会影响记忆力,我才能忍得住那些疼啊!”
我含着眼泪,欣慰地笑了。看来,在吃苦这一点上,儿子早早地就学过去了。经历了这些,我相信,我们一家会有个更好的未来。【本文来自知音旗下公众号:知音真实故事 ID:zsgszx118,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