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油腻的中年男人刷爆朋友圈,油腻中年话题成为了舆论热点。而随着《老年生活如何过——70后向往自由,60后注重健康》一文的刊发,70后瞬间成为老年群体,与此前的32岁老来得子、枸杞保温杯等现象结合,再次引爆中年危机话题。
那么中老年的年龄界限如何划分;产生中年危机的源头到底是什么;70后是否真的就认可自己步入老年;油腻的中年男人看的到底是身态还是心态?凤凰网评论部特别策划【你中危了吗】系列评论,从不同角度解读当下“中年危机”。
文丨特约评论员 寇步金
冯唐炮制的“油腻中年”一文已经占据朋友圈一周左右,一开始是恶心中男,而后是有抗议这一标签的,打来打去,以致于冯唐本人也被对方辩友狠命用小匕首戳。考虑到中国之大,信息鸿沟千条万条,“油腻中年”的恶意想必随着传播的梯次,还在社会上余音袅袅。
恶心中年男人,以及相反方向的中男维护,相爱相杀,冯唐不是第一个挑明这一现象的人。他对中男的攻击,摆明了契合一个非常适宜传播的舆论环境,是对社会口味需求的精准满足。到底是“油腻中年”催生了环境,还是环境催生了类似恶意的高涨,一时也难解难分。
无论是攻击中年还是反抗污名,都容易陷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观点泥沼当中,进而成为这一股不名誉现象的组成部分。所以,想要做一点工作的,是想探讨下这股针对中男的攻击风潮、或者说这组笼罩在国人头上、相互憎恶的年龄标签,其背后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熊孩子”“青春就是昏睡”“油腻中年”“坏人变老”这些便签已经随处可见,一条龙似的贯穿在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这种刻板印象,时刻会杀入舆论场合,左右事件的节奏,在观点市场上见鬼杀鬼、遇佛杀佛,如入无人之境。
中危问题或者说对中年男的攻击,粗略看有两条线索,一是知识分子这条线上,危机从五岳散人的微博开始蔓延,“作为一个有点儿阅历,有点儿经济基础的老男人……除非是不想,否则真心没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儿,或者说睡上也行”,中危问题成了炮火倾斜目标。
知识分子对女性的赏玩态度,激起女权分子的激励呛声,但女权所做所为,也还是因势利导。GQ杂志发表《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接下来就是马东与许知远的对谈争议,俞飞鸿那一集被翻腾出来,许知远的容貌被融合到了讨伐中男精神世界的檄文当中。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群落的舆论历史中,这种对“女青年”的把玩式笔法,其实早就在男人帮抬举柴静那时候就出现了。彼时,这种笔法被以为是高明,透着这些人玩转社交媒体时故意展露的炫耀神情。可光景不长,这帮人就被他们津津乐道的写法反噬,并被贴上中危问题的标签。
这是知识分子这条脉络,在另外一个进路上,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在知识分子文人毫无忌惮地在公共空间展现时政观点以外的评判嘴脸时,大众文化中主要由新生代凝聚起来的戏谑文化也在发展当中,“30岁老来得子”“90后中年”“枸杞保温杯”等渐成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油腻中年”正是这两股潮流的汇合,碰撞出的不是火花,而是“油腻”。这一次汇流,将针对中男的攻击最大程度公开化,一些评论试图从文化、社会心理、传播学角度去归纳、定性,当然也都有,可一个政治维度的定性恐怕也是不可少。
从因果逻辑上分析,对中年男的攻击与对公知形象的没落是勾连在一起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今覆盖各个年龄段的标签,其灵感恰恰是这帮自由主义者提供的,那就是“坏人变老”这个元标签。它本是自由主义者的杂耍,是在高谈阔论之外的观点的碎屑,是批判公权之外,很有节制地将批判性延伸到社会议题的尝试,浅尝辄止的尝试。
为什么这么讲?按照现今被推上中年祭坛的公知的原则,他们在公共言说中信奉“恶猜公权、善待私权”的信条,当言论攻击触及官方身份之外的私人身份——哪怕确有瑕疵——他们也会收手。“坏人变老”是这种历史言论对社会领域浅层次的延伸,但它显然启发了更多人。
在中男把持舆论场主基调的时候,他们主要的言论作战区域集中在监督公权,但是对社会倡导多元化的宽容,厉声责难公权、轻轻责备私权成为一时之选。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众舆论场,而“大众”在这个场域很快蝶变、迭代,并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充当听众到拿起喇叭。
说的明白点,指向中年的密集攻击,其阵地不是任何话语的简单继承,而是在自媒体为典型的大众文化阵地中喷射怒火。这射向中男的一箭之仇,来自于泛媒体青年对旧媒体势力的拒斥,他们以亢奋的复仇之剑试图出人头地,吹响了炮打中男的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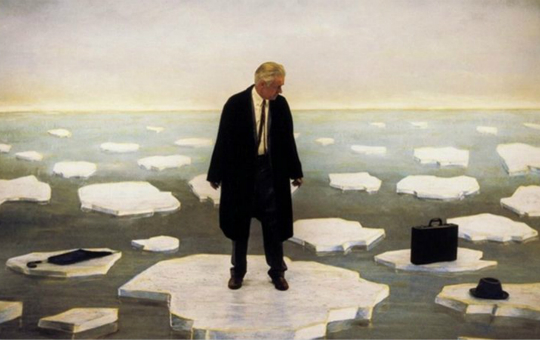
那个令中男胆战心惊的“号角”究竟是什么冷铁制成?新媒体群落又是如何获得它?那撕裂天空的节奏又是何人谱写?这些都是值得细究的问题,可明白点讲,谁也无法追究得太细。但分明是,个人主义的灵魂也在号角声里逃遁,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变化。
正如上述所言,对中年男的攻击,一个最大的利器是不再是经验主义的。由此,这中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裂,经验层面的断崖。“油腻中年”作为标签,在其背后炮烙着一行字:经验不再重要。这就带来两个很重大的命题,一个是关于世代,一个关于记忆。
撇除儒家三纲五常等传统意义,世代这个概念是有政治性的,它意味着新的世代可以能动地处理政治。所以,世代天然地具有政治想象,即使是在“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样的描述中。但在攻打中年“堡垒户”时,可以发现世代正在失去它更多的想象力,世代的多元轮替被抹消。
中国人对“新”的崇拜,时刻见诸于对年轻人的信任与寄托当中。在至少五年前,新世代都被看作是社会进化的主力,是进步的代名词,是比“少年强则中国强”意蕴更为广泛的心领神会。可在年龄段的互相憎恶中,世代的互通淤塞,关于世代的想象变得狭窄。
试想一下,你怎么对“熊孩子”朗诵“少年强则中国强”?你如何对“昏睡的青春”唱出捍卫权利的歌?你怎能指望“油腻中年”担负起社会的壮阔基础?你何以在“坏人变老”的诅咒中自处?“长大后就成了你”,这句歌词的惊悚含义一目了然。
焦躁不安又互相践踏的世代关系,由此带来世代间的疏远、隔离,经验作为信息流、尤其是是作为记忆的胶囊,也就无法从上一代导入下一代的脑子里。攻击中男的射手们,以激烈的厮杀攫取视觉效果,但又不可避免地失去“记忆”,尤其是长时记忆。
其实,年轻崇拜并不是个问题,既然每个人都会年轻(过),年轻崇拜也算是很公平的了。问题就在于,这种年轻的前景,是以多种多样的丧失为前提——哪怕丧文化被发明出来以抵御此间早晚知晓的失去,也还是不能治愈。人是由记忆塑造的,失去记忆,何以为人?
当然,无论是世代间人为的隔膜,还是以经验沦丧为标志的记忆脱节,可能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样看来,对中年的攻击,以及弥漫开来的中危问题,考虑到世代与记忆作为代价,它的复仇本质是一览无遗的。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无非是依次迈向断崖,在停滞的想象中葬送肉身。
总之,一个散沙状态的、即所谓原子化的个人,是前中危时代担忧的中心思想,生怕个人无法结成完美社会,最多用消极自由安慰犬儒。而一个相互厌恶、彼此隔绝的世代关系,不只是取消了个人,更将强烈的恨意散布人际,隔断记忆,阻断视野,以“油腻”为名的、讲政治的大合唱中,终于将“复仇”正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