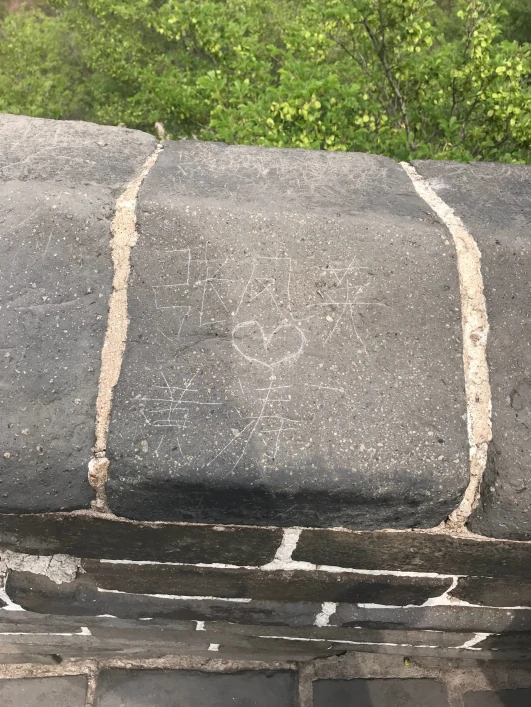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近年来出版多种;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
秦晖先生谈及辛亥运动时曾经这样比喻:“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实际也存在着这一现象。
随着一批著作的面世,如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以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等,五四运动的真相更为清晰。
认识五四
源于政争,知识分子角色不可忽视
在行动上,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而为。而在原因上,有一个因素往往容易被忽略,则是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知识分子或政客发挥的作用。
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8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国作战,但未经国会通过。按照北京政府规定,1918年5月20日举行众议院选举,6月10日复选,6月20日参议院选举。由于国民党拒绝参加,安福系的徐树铮暗中指示各地不得选出研究系议员。7月底选举结束,选出安福系议员300名,旧交通系议员100名,研究系议员仅20多名。自此,研究系与段祺瑞集团由盟友变为政敌。9月中旬,北洋系统元老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11月2日,众议院通过对德、奥宣战议案,11月6日,参议院通过议案。6天之后,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段祺瑞因力主参战,一时成为功勋人物。
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18日提出的14条纲领,讨论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巴黎和会将在一战结束后举行。威尔逊是学者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主张在中国引发强烈共鸣,中国人因此对巴黎和会期待很高。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总统府成立了外交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研究系的汪大燮、林长民两人。1919年2月16日,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主体也是研究系人员林长民等人。
几次名单变更之后,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终于确定,五位全权代表是陆徴祥、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另有胡惟德、颜惠庆等人。巴黎和会开幕前后,国内一批社会名流也汇集巴黎,他们都是皖系和安福系的政敌,其中包括研究系的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
其时,中国铁路多由外资或者借外债修筑,英美与日本在控制中国铁路上竞争激烈。一战期间,日本攫取了中国铁路利权。一战结束后,英美希望打破日本对中国经济实业的垄断,林长民及外交委员会支持英美,希望打破日本独吞山东及满蒙路权的策略。而日本则得到了交通系、安福系的支持,曹汝霖则为新交通系首领,支持日本,双方争执不下。1919年5月10日,英、美、法、日银行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12日达成新银行团八项协议。这一问题,与巴黎和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和会外交及国内政争的复杂局面。
由于美国支持,中国在和会收获甚多,如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成为创始会员国。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中就山东问题发言,他依据国际法,分七个层次驳斥了日本的法理依据,内容精彩,层次分明,获得了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但是,日本坚持“条约神圣”,逼迫英、法等国实践承诺。美国受到英、法牵制,以及意大利威胁退出和会的影响,对中国的支持力度,有所削弱。而日本又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原则,这严重威胁到威尔逊最关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问题。
4月22日,陆徴祥、顾维钧应邀参加美、英、法、意、日五国会议(日本代表没有出席)。讨论日本的要求:在对德合约条款中,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抽出,使其不从属于中国问题。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开会决定对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但对日本承诺归还中国的条件进行讨论。此外,威尔逊努力要日本承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并限制其在山东的经济特权。
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交于日本。日本代表牧野做了半官方口头声明: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中国,惟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业主,专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换言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威尔逊对此声明表示满意,三强决定,将日本建议条款纳入对德和约156-158条。
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认为,“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从事实上来说,在一战中,协约国和日本战胜德国,均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付出了代价。英国外相巴尔福认为,“而中国未出一兵未花一元,却收回了许多他自己无法取回的权利。”
4月24日,梁启超电告国民外交协会,“汪林两总长专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从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这封电报,林长民拟成一篇短稿《外交警报敬告国民》,5月2日发表在与研究系喉舌《晨报》第二版。林长民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 年5月11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刊登的《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
“三日这一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国民对日本人取最坚决的对待,更于国耻纪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 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这举动议决的时间, 已经夜十一点钟。”这两个会议,邵飘萍都参加了。
据罗家伦回忆:
到五月一、二号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眞、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羣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卽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次日,五四运动爆发,三千多名被学生参与游行,标语有“诛爱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并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当日,警方逮捕了32人。由于五四运动,在国内,经手对日借款、签署山东问题换文的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国贼”被罢黜,在外交方面,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5月5日,林长民与汪大燮、王宠惠联名力保被捕学生,并帮助学生成立了联合会,还上街演讲,抨击曹汝霖等人卖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屡次受到列强欺凌,对此次巴黎和会,怀有过高的期待。一旦这种期待落空,就必然由失望转变为反弹,变成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政客如何介入政治?政治活动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反思五四
激进思潮,中断了文化的启蒙
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被捕的学生很快被释放,放火烧毁曹宅的学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成为所谓“外交失败”的替罪羊。在这场运动中,学生发现了自身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此后,学潮频繁产生。
台湾学者吕芳上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统计,1919到1929年,共发生学潮248起,反对列强的仅有17起,所占比例仅略高于5%。反对教职员的17起,反对校长的99起,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的30起,不满学校设施的有37起,反对学校收费的有20起。1921年,就因为此前免费的讲义要每册收费两角,北大学生就攻击校长。另有12起因为学生冲突,5起因为教员冲突所致。
吕芳上认为,“五四”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学生自治逐步扩大,继而演变为学生治校。这使他们有勇气和力量进行社会和政治抗争。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居然成功废止考试,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当时觉得,考试是压迫、残害人的制度,主动放弃北大学位,并发表了《反抗“考试”宣言》。在吕芳上看来,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民族主义高潮,但除了拒签合约之外,看不出什么重大新的效果。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直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同。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也做了这种划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和救亡的互动,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后屡遭挫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此时,俄国向中国输出了革命,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救亡压倒了启蒙”。
新革命史学者王奇生的研究证实,五四让新文化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世纪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
“五四之后的五六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王奇生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指向于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而五四运动则指向于激进革命和群众运动。激进革命的兴起,中断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到今天,我们应当对于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做出理性的反思。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到列强的欺侮,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其他阶层,都处于一种深层的焦虑之中,这种峻急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建设未必有利,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也难有裨益。
让五四回归历史的原型,无疑有助于中国人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